爱尔兰的许多租房者都生活在恐惧之中,担心环境的一个变化就可能让他们一夜之间无家可归。
据首席执行官约翰-马克·麦卡弗蒂 (John-Mark McCafferty) 称,人们联系无家可归预防组织 Threshold 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收到了房东的驱逐通知。他们遇到的问题是什么?他们无处可去。
根据最新数据,私营部门出租的房屋约有 33 万套。如果房东想出售房屋或让家庭成员搬进来,租户就无法避免失去栖身之所。
“在爱尔兰,我们有一种叫做‘无过错驱逐’的做法,这意味着你可能被驱逐,尽管你没有过错,”都柏林理工大学住房讲师 Lorcan Sirr 说道。“在每个国家,如果你不付房租,或者你把房子弄得乱七八糟,你都可能被驱逐……但在极少数国家,你仅仅因为房东的岳母想每月在房子里住两个周末而被驱逐,”他说。
还不包括常见的生活变故,比如房产不合适或租金太高——比如感情破裂、室友决定搬出或新生儿的到来。
在这种情况下,要找到另一个住处并不容易,由于供应不足,租房者不得不在位置和便利性上做出妥协——前提是他们实际上可以找到另一个可能满足他们需求的地方。
此外,根据住宅租赁委员会 (RTB) 的数据,仅 2023 年租金就上涨了 9%,许多人发现他们已经完全负担不起租房费用了。
RTB 的 2023 年最后一个季度新租约价格指数显示,全国标准化平均租金为 1,415 欧元,平均租金从都柏林的每月 1,972 欧元到利特里姆的 740 欧元不等。
[ Threshold survey finds three-quarters of tenants struggle to pay bills after covering rent ]
[ Ireland is spending big on housing. So why is the sector still in crisis? ]
一些别无选择的人可以向父母求助,但当涉及到所谓的家庭安全网时,人们会做出许多假设,西尔说:“一方面,人们有家人可以搬回去,而且人们还认为父母希望他们回来,但往往他们并不希望。”
此外,“你的父母可能住在文特里或凯里,而你可能在都柏林工作”,他说。在许多这样的情况下,“有没有父母可以搬回去住并不重要”。
我们与租房者谈论了不稳定的租房市场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
“这就是没有自己的空间,无法在不打扰别人的情况下做事。”Joshua Manuel-Oni(29岁),都柏林
乔舒亚·马努埃尔·奥尼 (Joshua Manuel-Oni) 在都柏林北部的家中:“事情总是让人感觉是暂时的。” 图片来源:Dara Mac Dónaill/爱尔兰时报
约书亚·马努埃尔-奥尼 (Joshua Manuel-Oni) 在沃特福德长大,自 2012 年搬到都柏林大学攻读本科学位以来,一直在都柏林及其周边地区租房居住。他现在从事科技行业,与另一人合租了一套位于都柏林北部郊区的两居室公寓。这个地区离市区较远,比他想要的要远,但当时这间房间的价格在他可以承受的范围内。
尽管与现在的室友相处很愉快,但马努埃尔-奥尼表示,过去与陌生人同住时也曾有过一些尴尬的经历。例如,一个室友会邀请陌生人到家,并大声播放音乐直到深夜;另一个室友不遵守他的清洁标准,尤其是在共用浴室里。
他说,即使有志同道合的室友,分享仍然很困难。“就是没有自己的空间,无法在不打扰他人的情况下做事。”
住在城外,公共交通的缺陷也影响着他的日常生活。“我每个月要花钱最多的两个项目是住房和交通,如果这些费用大幅减少,交通得到改善,我会觉得爱尔兰是一个几乎令人惊叹、完美、美妙的居住地。但这两件事让我的生活变得如此艰难,”他说。
一边存钱一边租房太难了,你必须降低生活质量,尤其是如果你想自己做的话
— 约书亚·曼努埃尔·奥尼
曼努埃尔-奥尼与兄弟姐妹一起租房住了几年,感觉“还不错”。但自从他们搬到不同的地方后,“一切都感觉很短暂”。
当他租住的房间附带的床垫对他来说太小时,这种不稳定的处境使他陷入了两难境地,每当需要大笔购买时,这种两难境地就会重演:“你会想,‘如果我要在这里住五年,五年内花 200 欧元买一张床垫算什么?——这不算什么。’但如果你又想,‘我要在这里住六个月、一年或两年,我应该现在买东西然后经常搬家,还是等到下一个住处再买?’——我总是有这种感觉。”
曼努埃尔-奥尼表示,最终能够买房似乎不太现实:“试图同时存钱和租房太难了,你必须真正降低你的生活质量,特别是如果你想自己买房的话。
“即使有我能负担得起的地方,那也不是我想住的地方,也许我的朋友和家人也住在那里,所以目前这似乎不太现实。”
“我在政府部门工作,但我感觉自己被抛弃了,被忽视了”劳拉*(31岁),都柏林:quality(70)/cloudfront-eu-central-1.images.arcpublishing.com/irishtimes/WHX4X3BWNBHGNBTR5K62DEDMZU.jpg)
今年 5 月,劳拉第三次向当地议会陈述自己无家可归的情况。图片来源:Cathal O'Gara
*“劳拉”(化名)希望保持匿名,因为担心她在私人租赁领域寻找住房会受到影响。
今年 5 月,劳拉第三次向当地议会申报无家可归。此前,她被赶出了她在都柏林租了五年的公寓,因为房东决定出售这套公寓。劳拉在政府机构工作,经常上夜班,在轮班期间,她有几周时间睡在车里。
“我在那里感觉不安全,”她谈到州政府提供的紧急住宿时说,她被安排与另外两名妇女共用一个房间的铺位。她觉得在非工作时间上下班时打扰其他妇女很不舒服,最让她反感的是住宿中心的工作人员晚上进入房间的政策,她说,“检查是否有人吸毒过量 [overdosed]”。
劳拉不得不把车停在不同的地方,以免引起居民的注意,她在住宅区、凤凰公园和她以前停放多年的旧公寓附近停车,“所以我觉得在那里很安全,”她说。由于身高 5 英尺,她说她躺在后排座椅上试图睡觉。
除了上班,劳拉没有和同事谈论她的情况,因为她想让办公室成为一个可以让她忘记生活状况的地方,健身房是她唯一可以避开汽车、锻炼身体和使用淋浴设施的地方。
她把其余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寻找住处上,不断查看房源清单,寻找她能负担得起的房间、公寓、单间公寓和公寓,这些公寓的租金加上她的住房援助金 (Hap) 津贴。她说,到目前为止,她已经“看过好几次房子了”,但“运气不佳”。
除了在私人租赁行业摸索,劳拉自 19 岁起就一直在社会住房的候补名单上,每周五都必须登录市议会的“基于选择的出租”平台,申请符合条件的社会住房。她认为自己在 12 年内申请了至少 400 套住房。
可能不得不再次搬家的不确定性始终存在
— 劳拉
“前几天我对 Threshold 说,就像我梦到的创伤一样 [former taoiseach] 前几天晚上,我梦见自己在对他大喊大叫。我肯定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尤其是这是我第三次 [presenting as homeless]我从事政府工作,但我感觉自己被抛弃、被忽视、被遗忘了。”
劳拉说她没有家庭保障。她的父亲住在英格兰的一家养老院,而她的母亲是首都一所工业学校的“幸存者”,“这让她染上了毒瘾,这主要是因为国家给她这一代人带来的创伤”。
“每当我想到这件事,我就感到很生气,因为 [of] 这些对世代的影响 [industrial schools] ……这就是它对我家几代人的影响。我努力让自己摆脱它。多年来我一直在努力让自己摆脱它。”
[ Housing crisis: ‘We lived on €20 a week. We saved absolutely everything. There was no avocado toast’ ]
劳拉担心,即使她确实找到了出租房产,她也有可能很快会发现自己处于同样的境地:“我一直担心这种事情会再次发生,因为只要理事会需要向我提供房产,房东就会继续出售。”
最新消息:自从我们与劳拉交谈后,她在车里住了近一个月后,在私人租赁领域找到了一套公寓,她“欣喜若狂”,尽管她表示,“可能不得不再次搬家的不确定性一直存在”。
“我们对这一事实感到愤怒 [the landlord] 没有和我们讨论这件事,只是发了驱逐通知。杰米·科尔曼(44岁),科克市:quality(70)/cloudfront-eu-central-1.images.arcpublishing.com/irishtimes/QXWJCEVHUJFGXERYKWYCJW2QQE.jpeg)
Jamie Coleman 和 Justyna Byczkowiak,科克。
由于房东决定从国外短暂居住回国,出租车司机杰米·科尔曼 (Jamie Coleman) 和他为一家电子商务公司工作的伴侣贾斯蒂娜·比茨科维亚克 (Justyna Byczkowiak) (36 岁) 被赶出了科克市的一所房子,他们找了一套“有点低廉”的新出租房,科尔曼说。
科尔曼说,当房东非正式地告诉他们,他们可以在这里住六年,直到他自己的孩子出国留学归来时,他们一家人以及他们的两个女儿和科尔曼的儿子就决定把这里变成自己的家。
“我们自费装修了房子,最后把家具都配齐了,所以我们借钱买了所有东西。只留下了一件东西,那就是一张咖啡桌,没有别的了。我想我们借了大约 15,000 欧元。”
他们为这所房子投入了大量精力,填补了墙上的凹痕,并将整个房子粉刷一新:“邻居们以为我们想买下它,”他说。
科尔曼与房东建立了非正式的关系。他们会聊聊彼此的生活,科尔曼告诉房东,他们一家人非常喜欢这套房子,并询问他是否有可能从他那里买下它。“他说他不会拒绝,因为我告诉他我无法获得抵押贷款,但我知道如果我们达成交易,我就能负担得起。我说你现在可以嘲笑我,或者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但他说一切皆有可能,所以我们到时候再谈。”
我们没有安全感。尽管我们在这里很开心,我们喜欢这里——但我们感觉不安全
— 杰米·科尔曼
不幸的是,对于科尔曼和比茨科维亚克来说,这种可能性被打破了,因为他们在搬进来五年半后,就在他们即将开始家庭度假之前收到了驱逐通知。科尔曼说:“起初我们很恐慌。我们很生气,因为他没有和我们讨论这件事,只是给我们发了律师的驱逐通知。”
科尔曼说,他随后给房东发了一封信,当房东没有回复时,他又发了一条短信,再次询问这对夫妇是否可以买下这栋房子。房东告诉科尔曼,他不会出售这套房子,他会自己搬进去住。
[ My landlord is not acting on a ruling from the Residential Tenancies Board. What can I do? ]
科尔曼后来从以前的邻居那里得知,他们搬走后,另一个房客搬进了这所房子,而不是房东本人。
这对夫妇随后决定向 RTB 起诉房东,因为他未能确定该房产的预期居住者。他们向 Threshold 寻求指导,Threshold 向他们介绍了整个过程。RTB 裁决员裁定,房东有责任向这对夫妇支付 8,378 欧元,因为“违反了《2004 年住宅租赁法》第 12 条规定的房东义务”。
这家人在乡下找到了一套新的出租房,他们很满意,但这里不如原来方便,现在他们十几岁的孩子要靠他们载去见朋友。
科尔曼说,他们夫妇无法获得抵押贷款,因为“我们有很多开销”,而且“我们发现很难获得贷款”。
“我们有孩子,我们尽力给他们最好的生活,”他说。“当然,当我们必须注意钱的时候,我们会注意钱,但是,比如,我们最小的孩子,她去上舞蹈课,她也去游泳——这些都要花钱。我们的大女儿,她去骑马,这是她最喜欢的事情,就是马,我们尽力不剥夺她的这种权利。
“谢天谢地,我们在住房名单上,”科尔曼补充道,“但同样,那里什么也没有。”他说,他的神经科医生写了一封信,描述了压力对他作为一个多发性硬化症患者造成的不利影响,“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在名单上的排名。
最近,他们收到了负责他们现在住所的租赁中介发来的一封挂号信,“我们的心都沉了下去”,他继续说道。他以为这可能是另一封驱逐通知,“我们俩立刻感到恶心”,但结果却是例行建筑检查通知。
“我们总是有这种感觉。我们没有安全感。尽管我们在这里很开心,我们喜欢这里——但我们感觉不安全。
“你知道,我们只是在等待。比如,下次什么时候会发生?”
“我们支付的租金与抵押贷款相同,但我们却无法获得抵押贷款,这真是太疯狂了。”Eliza Kelly(31岁),戈尔韦市:quality(70)/cloudfront-eu-central-1.images.arcpublishing.com/irishtimes/UWVNUXC6IRFXHIUX5CCK77MURI.jpg)
伊丽莎·凯利 (Eliza Kelly) 在她工作的健身房,位于戈尔韦郡奥兰莫尔。照片:Andrew Downes/Xposure
来自基尔代尔的伊丽莎·凯利 (Eliza Kelly) 自 2012 年搬到戈尔韦市学习以来就一直租房居住。她现在在一家健身房担任私人教练,在市中心的一套公寓里租了一个房间,与另外两人合租。
她说,现在的住处可能会有点尴尬,因为房东单独出租房间,所以她无法决定和谁住在一起,尽管目前为止一切都还好。“当你还在上大学或更年轻的时候,可能还好,但当你年纪大一点的时候,你真的不想每六个月就和不同的人住在一起。”
凯利说,她对住房的状况总是“感觉有点临时”,“房子随时可能被抽走——你安顿下来后,有人决定搬家,或者房东决定卖掉房子,然后你又要出去找房子了”。
我们拿不到抵押贷款,尽管过去 12 年来我一直在付房租
— 伊丽莎·凯利
她认为自己很幸运,能以现在的价格支付房租。“我租的第一个房间是 375 欧元,现在这个是 550 欧元 [a month]。这甚至没有翻倍,但我想大多数人支付的费用几乎是 10 年前的两倍。”
她说,如果她被赶出现在的住所,她甚至不会考虑再次在戈尔韦市租房,因为目前的房租价格已经很高了。(截至撰写本文时,戈尔韦市地区共有 99 个合租房源 达夫蒂,价格从每月 600 欧元起,最高可达每月 1,100 欧元。)
“我们支付的租金与抵押贷款金额相同,但我们却无法获得抵押贷款,这简直太疯狂了,尽管过去 12 年来我一直在支付租金,”凯利说。“你会认为这对银行来说是一个合适的记录,但事实并非如此。”
“还有整个养狗的情况,”她叹了口气补充道——“你真的不能养狗。”
“我不能借足够的钱买房,所以我必须拿出更多的钱。”大卫*(38岁),科克市:quality(70)/cloudfront-eu-central-1.images.arcpublishing.com/irishtimes/WHX4X3BWNBHGNBTR5K62DEDMZU.jpg)
尽管 David 的年收入约为 7.5 万欧元,但他至今仍买不起房子。图片来源:Cathal O'Gara
*“大卫”希望保持匿名,以保护亲近人的隐私。
大卫是来自科克市的一名 IT 工作者,去年婚姻结束后,他搬去和 70 多岁的父母同住。
他和前妻以及患有智力障碍的儿子一直共同在城里租房居住;由于前妻需要全职照顾他们的儿子,因此她正在申请国家财政援助,以便继续为她自己和儿子租房。
尽管 David 每年的收入约为 75,000 欧元,但他至今仍无法买房。当他向银行询问自己的抵押贷款资格时,他惊讶地得知,他支付的子女抚养费被视为长期贷款,因此他的允许收入将使他有资格获得约 170,000 欧元的抵押贷款。
我很可能需要支付远超正常 10% 的首付,因为我无法借到足够的钱买房
– 大卫
“所以,现实情况是,这笔钱根本不够我买得起房子,除非我去很远的地方……而我儿子住在哪里,他的学校在哪里,所以我不能走太远,”他说道。
他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能否存够买房的钱:“我很可能需要支付远超正常 10% 的首付,因为我无法借到足够的钱买房,所以我必须拿出更多的钱。”
然而,他仍然希望事情会顺利解决,他的目标是为自己和他的儿子建立一个稳定的基础。
“目前他有一栋他知道是他自己的房子——理想情况下,几年后我希望他能有两栋。”
需要免费和保密的住房问题建议的租户可以拨打免费电话 1800454454 联系 Threshold 或访问 阈值.ie/get-help。

:quality(70)/cloudfront-eu-central-1.images.arcpublishing.com/irishtimes/ZJSOHZPORRCJBLLGOOACO6YFBA.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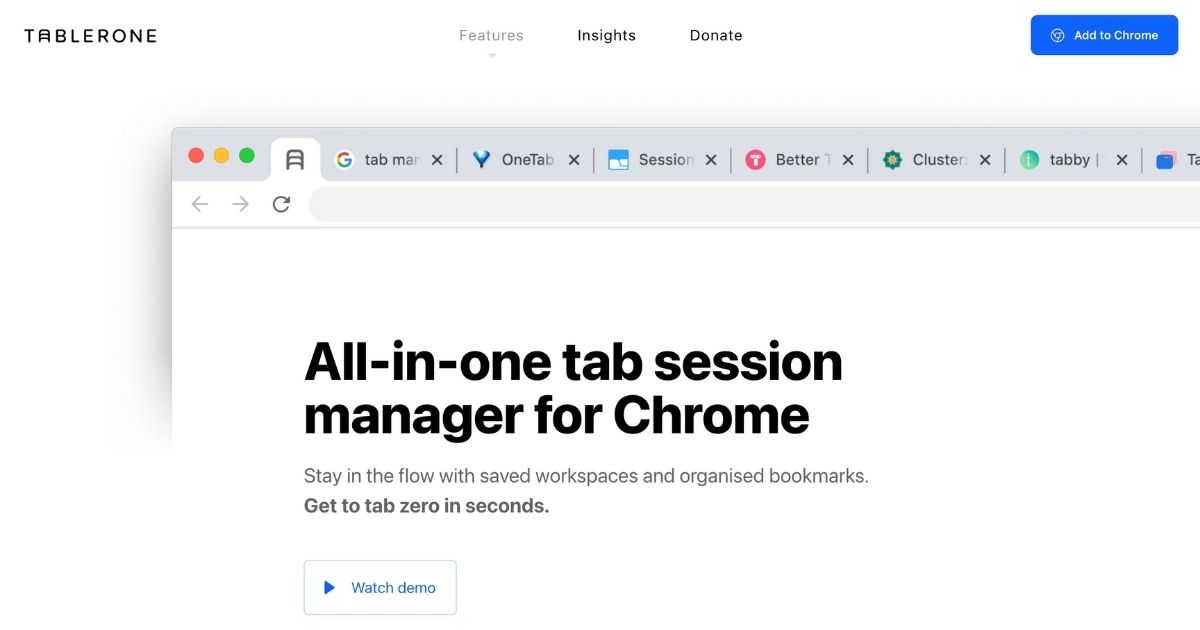






:quality(70):focal(2514x915:2524x925)/cloudfront-eu-central-1.images.arcpublishing.com/irishtimes/X4KDDSSFFRGMLDVJIWJWSVD2UE.jpg)

:max_bytes(150000):strip_icc():focal(683x282:685x284)/Lauryn-Hill-063024-a091e32f1ddd41cfacf7f9e8a707df0d.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