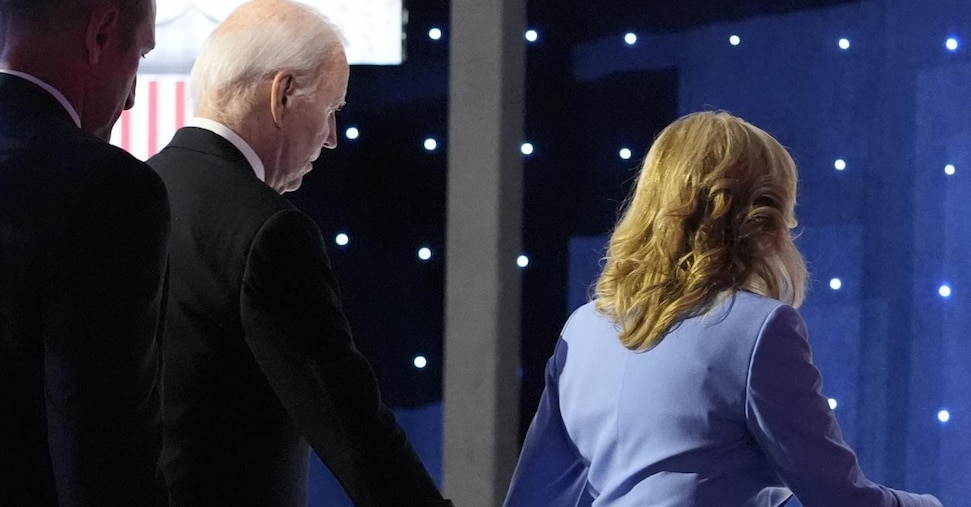2021 年 10 月,一架飞往白俄罗斯的飞机。乘客中有一对叙利亚夫妇,巴希尔 (Jalal Altawil) 和阿米娜 (Dalia Naous),他们带着三个孩子和巴希尔的父亲 (Mohamad Al Rashi) 一起旅行;他们逃离了国内的战争和迫害,希望最终能与瑞典的亲戚团聚。在飞行过程中,阿米娜结识了一名阿富汗妇女莱拉 (Behi Djanati Ataï),她和他们一样,正在国外寻求政治庇护。前方是一段漫长而危险的旅程:在明斯克降落后,一家人将被送往白俄罗斯-波兰边境,这是他们进入欧盟的入口——这条走廊几个月前才向移民开放。“这条穿过白俄罗斯的路线是上帝的恩赐,”阿米娜一边说,一边在飞机下降时照顾她最小的孩子。即使是一个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的人也会感觉到她大错特错。
《绿色边界》就是这么开始的,这是一部极具震撼力的新电影,由 75 岁的波兰裔电影制片人阿格涅丝卡·霍兰执导,她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为那些饱受战争摧残的人拍电影。(她与卡米拉·塔拉布拉和卡塔日娜·瓦尔泽查合作执导了这部电影,并与马切伊·皮苏克和加布里埃拉·扎扎基维茨-谢茨科共同撰写了剧本。)片名指的是白俄罗斯和波兰交界处的一片茂密的森林迷宫,尽管我们只在开场俯拍镜头中短暂地看到了郁郁葱葱的树木。片刻之后,图像变为黑白,并保持不变。这个决定有一丝仁慈;当巴希尔和阿米娜最大的孩子努尔(泰姆·阿詹饰)触碰到铁丝网围栏并痛苦地大叫时,你看不到他手掌上的伤口渗出红色。 但尽管电影在直观性方面有所欠缺,但它却在紧张感和恐惧感方面有所提升,因为这家人——还有加入他们的莱拉——被武装士兵强行越过边境,士兵的愤怒声音汇成一片喧嚣的叫喊声。另一边等待着他们的是片刻的宽慰:“我们在波兰!”莱拉大喊道。但他们的旅程——以及他们的噩梦——才刚刚开始;实际上,他们从一个战区逃往另一个战区。
这些角色是现实生活中的虚构人物,他们自 2021 年以来应白俄罗斯独裁者亚历山大·卢卡申科的邀请,通过白俄罗斯涌入波兰。在开辟全球移民危机的这一特殊战场时,卢卡申科将难民作为对抗欧盟的武器,目的是破坏自由西方的稳定,在世界范围内煽动右翼民族主义和反移民言论。正如霍兰德提醒我们的那样,这些策略是有效的。在一个场景中,背景是波兰边境服务站,一名强硬派官员指责卢卡申科发动“经典混合战争”,并敦促他的警卫不要对移民表现出任何怜悯,他贬低移民是罪犯、恐怖分子和性变态者:“他们不是人,”他说。“他们是实弹!”
事实证明,这些子弹不仅可以随意重复使用,还可以朝另一个方向发射。莱拉、阿米娜和其他人被波兰边防警卫抓获,再次被强行塞过边境进入白俄罗斯,开启了一个可怕的循环。霍兰德不无幽默地不断更新地点卡——“白俄罗斯”、“波兰”、“白俄罗斯”、“波兰”——人物在这个森林沼泽的地狱之环中来回穿梭。一路上,他们与其他难民一起被抛在一起,其中许多人已经在同一地缘政治困境中困了很久,他们的身体和精神被饥饿、口渴、暴露、疾病和疲惫所折磨——更不用说他们在双方遭受的殴打、勒索和种族虐待了。 (在电影情节发生的几个月后,即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最初几周,近两百万乌克兰难民受到了波兰人相对热情的欢迎——这是一种种族主义的双重标准,霍兰德在简短而尖锐的尾声中对其进行了戏剧化描述。)
这些细节在迅速连续的痛苦画面中融合:缠着绷带、起着水泡的脚、毫无用处的电量耗尽的手机、在寒冷和雨中挤在一起的家人、阿米娜拼命地将植物上的晨露挤进女儿加利亚 (塔莉亚·阿詹饰) 的嘴里。一幕又一幕,《绿色边界》是一部充满毁灭性智慧、惊人视觉清晰度和异常强烈愤怒的作品。尽管片长长达两个半小时,但画面仍以极快的速度向前推进;霍兰德电影制作的绝对灵活性直接表达了她的同情心。她和摄影指导托马斯·纳乌米克 (Tomasz Naumiuk) 让摄影机保持颠簸、摇晃的动作,而不会牺牲连贯性;帕维尔·赫德利奇卡 (Pavel Hrdlička) 灵活的剪辑从不停留超过必要时间。 即使情节发展到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程度——比如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场景,涉及一名怀孕的索马里难民(乔莉·姆班杜饰),但电影并没有夸大或过分强调。它让那一刻的痛苦得以呈现,然后转向下一个场景。
与此同时,荷兰这位目光敏锐的人道主义者毫不畏惧地让故事有呼吸的空间,或者给我们一些自然的喘息:祖父坚持在荒野中铺开祈祷垫,这让他的儿子不屑一顾;努尔和莱拉之间温暖的融洽关系,他们在森林里跋涉时,莱拉给努尔上英语课。电影在每一个转折点都令人信服地唤起了一种混乱的状态,但又不屈服于它,因此从混乱中出现了一种可怕的清晰。这是一个系统性残酷的故事,你可以从角色忧心忡忡的脸上读出这一点:看看巴希尔和另一位难民之间冷酷的眼神交流,这是对他们两人即将面临的艰难命运的无声警告。或者想想莱拉在意识到一位友好的波兰农民刚刚给了她食物和水,也刚刚向当局告发了她时,她责备的目光。 霍兰德提醒我们,大规模野蛮行径的形成依赖于个人的共谋和背叛行为。即便是最彻底的不公正,也是在人性层面上实施的。
去年秋天,《绿色边界》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首映,获得了评审团特别奖,霍兰德也因此获得了几十年来最热烈的评价。但波兰政府官员对这部电影的评价并不高,许多人认为这部电影是纳粹宣传片,这太荒谬了(而且很可能是他们没有看过这部电影)。霍兰德的祖父母死于华沙犹太区,母亲是天主教徒,是 1944 年华沙起义的抵抗战士。这已经不是霍兰德第一次被左右翼的意识形态对手指控煽动反犹太主义了。即使是她 1990 年的杰作《欧洲欧洲》(最独特、最有震撼力的大屠杀剧之一),也因敢于讲述所罗门·佩雷尔的真实故事而受到批评,佩雷尔是一名波兰犹太人,在战争中身穿希特勒青年团制服幸存下来。 霍兰德最伟大的电影主题是勇气、恐惧、本能、算计和纯粹的运气的结合,这些因素都要求霍兰德能够在独裁政权下生存,更不用说反抗独裁政权。她之所以成为一名出色的政治艺术家,是因为她愿意直面这一主题,不回避黑暗的讽刺或令人不安的道德复杂性。她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完全不人道的压迫者或完全无辜的受害者的谎言。
在《绿色边界》中,压迫者的面孔是扬 (托马斯·沃索克饰),他是波兰边防警卫之一,我们可以看到他强迫难民穿过无休止的严酷考验。在霍兰德的叙述中,他只被给予了一小章,并且得到了极少的同情。扬显然很紧张,因为家里的妻子怀孕了——与那位索马里妇女的情况大致相同——而且他对自己的工作很矛盾。虽然他折磨自己手下的移民,但他这样做时不像他的同事那样有明显的热情。但霍兰德坚持认为,微薄的良知是不够的,她有意将扬与另一个角色茱莉亚 (玛雅·奥斯塔舍夫斯卡饰) 进行了对比,茱莉亚是一位丧偶的波兰治疗师,住在树林边缘的一所房子里。正是茱莉亚一天晚上在沼泽地里听到了莱拉的呼救; 在一系列既令人激动又令人沮丧的事件中,她如何应对,改变了电影的进程和她的整个人生。她被激励起来,加入了一群意志坚定的年轻活动家,主动提供自己的房子和汽车,并与他们一起前往森林,为难民提供食物、水和医疗服务。
朱莉娅的英雄气概令人振奋,但霍兰德的坚强意志却体现在她对角色决定的解读上,她做出的决定并非一个美好的结局,而是一个艰难的开始。从这一点来看,《绿色边界》成为了一部引人入胜的关于激进主义和抗议的电影。朱莉娅了解到“禁区”的限制,救援人员被禁止进入,以及法律漏洞可以阻止移民立即被驱逐出境。她还意识到,即使是最强大的人道主义努力也收效甚微。挫败感导致激进分子之间无休止的争吵,其中包括两个性格鲜明的姐妹:谨慎而循规蹈矩的玛塔(莫妮卡·弗拉奇克饰)和充满挑衅能量的祖库(贾斯米娜·波拉克饰)。 在进行内心辩论时,“绿色边界”有时会让我想起霍兰德获得奥斯卡提名的大屠杀剧《黑暗中》(2011 年),该剧改编自真实故事,讲述了小偷利奥波德·索查 (Leopold Socha) 在波兰利沃夫的下水道中发现几名犹太人藏身时,差点英勇行事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战时生存不仅需要公开的勇敢行为,还需要无休止的谈判——在这种情况下,谈判涉及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躲藏者和隐藏者、盟友和潜在叛徒、自己和自己的良心。
朱莉娅的积极行动冒着掩盖莱拉、巴希尔、阿米娜和其他人命运的风险涌入叙事前沿。但霍兰德从未忘记她们,也从未忘记她们融入了她整个职业生涯中一直在讲述的更大的故事中——逃离、隐藏、失去和生存。每时每刻,《绿色边界》都发挥着如此不屈不挠的吸引力,并如此彻底地沉浸在冲突的政治戏剧性紧张之中,以至于即使是霍兰德的狂热崇拜者也可能会错过它在她生活和工作中的一些总体共鸣。这部电影讲述了没有国家存在的意义,不可磨灭地源于她自己破碎的民族认同感和她自己的政治异见历史。20 世纪 60 年代末,作为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名电影系学生,霍兰德因参加布拉格之春抗议活动而入狱; 多年后,1981 年波兰实施戒严,她移民法国,流亡多年,1989 年加入法国国籍。此后几十年,她的演艺生涯让她走遍了世界各地:她去了美国,参演过好莱坞改编的《秘密花园》(1993 年)和《华盛顿广场》(1997 年),以及电视剧《火线》和《劫后余生》;她又回到了中欧和东欧,在迷你剧《燃烧的灌木》(2013 年)和剧情片《琼斯先生》(2019 年)中戏剧化地描述了苏联极权主义的蹂躏。
最重要的是,霍兰的作品总是将她引向波兰——特别是波兰的森林,在她的手中,这片森林变成了一片充满恐怖和魔力的原始景观,被历史记忆的迷雾所笼罩,她的相机具有一种奇特的能力,既能唤起这些记忆,又能驱散这些记忆。这片森林是她 1985 年在西德制作的电影《愤怒的收获》的背景(但不是拍摄地点),讲述了一位波兰天主教农民在二战期间藏匿一名犹太难民的故事。《黑暗中》在下降到利沃夫的下水道之前,展示了森林中令人难以忘怀的场景,狡猾的小偷索查目睹了一群裸体犹太妇女被纳粹卫兵追杀。如今,在《绿色边界》中,霍兰回到了森林,将隐藏的恐怖带到了大众的面前; 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她有意识地将移民角色与大屠杀和其他灾难的受害者和幸存者置于视觉和历史的连续体中,驳斥了我们可能倾向于在一系列暴行(或一群人)和另一组暴行之间做出的区分。霍兰德提醒我们,现在的不公正都是历史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