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这是一个故事 史蒂夫·阿尔比尼 喜欢讲述他高中四年级的事情。 17岁时,他遭遇了一场严重的交通事故:骑摩托车时被汽车撞到,腿严重骨折。 在康复期间,他学会了他的第一件乐器——低音吉他,但这并不是故事的关键。 原来,在他住院期间,他接连接到同学的电话。 他们打电话并不是为了询问他的情况,或者祝他早日康复:他们非常恨他,所以打电话告诉他,他们很高兴他感到痛苦。
这是一个非常史蒂夫·阿尔比尼的轶事。 在他音乐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显然是在此之前的几年——他塑造了一个故意对抗、挑衅和两极分化的形象:正如迈克尔·阿泽拉德 (Michael Azerrad) 在他的美国后朋克另类摇滚的无与伦比的历史《我们的乐队可能是你的生活》(Our Band Could Be Your Life) 中所指出的那样,阿尔比尼的所作所为“含蓄地尖叫着‘请恨我!’”他在他的第二故乡芝加哥为粉丝杂志撰写了令人震惊的辱骂专栏,他的乐队 Big Black 的歌曲主题,甚至他们的方式唱片被包装起来(Albini 将刀片和鱼钩塞进了他们首张 EP Lungs 的袖子里;1987 年的 Headache 封面照片是一个用猎枪自杀的受害者,他的头被分成两半)。
他的下一支乐队 Rapeman 的名字令人震惊,他愿意对那些利用他作为唱片制作人的服务的艺术家说坏话,通常是因为在回避商业主义时未能达到他自己的严格标准以及主流音乐界:他公开斥责了这张让他作为制作人名声大噪的专辑,即 Pixies 1988 年的杰作《Surfer Rosa》,称其为“来自一支乐队的拼凑而成的捏面包,他们在最高价时只是温和地娱乐大学摇滚” ; Nirvana 在 1993 年的专辑《In Utero》中称赞他的表现“平淡无奇”。 阿泽拉德诠释了整个“请恨我吧!” 称之为“经常被欺负的人的先发制人的本能”。 不管是什么,它都奏效了:当英国品牌 Blast First 的 Paul Smith 去芝加哥签下 Big Black 时,他对与 Albini 一起漫步这座城市的经历感到惊讶:他报告说,每个街区都会有人破口大骂。阿尔比尼通常称他为“混蛋”。
正如阿尔比尼在晚年坦率承认的那样,他的一些挑衅行为——其中涉及仇视同性恋、种族主义和厌女症——现在看来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我出于舒适和特权的无知立场所说和所做的很多事情显然是可怕的,我遗憾的是,”他在 2023 年写道。话虽如此,他创作的实际音乐却常常令人惊叹。 Big Black 花了一段时间才开始起步——他们早期的 EP 中乐队慢慢地寻找自己的声音——但当他们在 1986 年的专辑 Atomizer 中大踏步前进时,效果令人瞠目结舌。 这首歌的歌词分别涉及虐待儿童、纵火——这也许是大黑人最著名的歌曲,六分钟的《煤油》——家庭暴力、腐败的警察和牲畜屠宰场,音乐提供了无情的、猛烈的鼓机和低沉的贝斯和两个吉他失真到听起来就像锯子撕裂金属一样(或者,正如片尾的拟声词所说,“咕噜”和“剥皮”),阿尔比尼喜欢用金属拨片弹奏吉他,这种效果被放大了。 这种效果可能是令人恐惧的,也可能是宣泄性的:无论哪种方式,大黑听起来都与众不同。
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 1987 年的《Songs About Fucking》甚至更好,但 Big Black 已经分手了,原因是吉他手 Santiago Durango 决定去法学院:“分手这种想法只有极少数的团体才会想到”,读到专辑的封套笔记。 阿尔比尼的下一支乐队,前面提到的 Rapeman,被证明是一种过分的挑衅——他们的演出遭到抗议者的纠察和干扰; 阿尔比尼(Albini)后来将他们的名字(取自日本卡通人物)称为“不合情理”,贝斯手大卫·西姆斯(David Sims)形容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音乐遗憾”; 他们唯一的一张专辑《两个修女和一个驮骡》有其原始的、摇摇欲坠的力量的时刻,但远没有《大黑人》那么始终如一的令人兴奋。 仅仅两年后他们就分手了。
但虫胶在阿尔比尼的余生中一直存在,受到了一致好评,这可能是因为他们不定期发行专辑的标准以及同样零星的现场表演很少下降。 另一个三重奏,他们在 Action Park 的首演表明这支乐队比他们的前任更微妙、更有棱角,甚至更成熟,尽管这些都是相对的:它非常强大,但你很难用任何其他东西来形容它,除了粗糙,而主题阿尔比尼的歌词问题仍然像以前一样令人毛骨悚然。 到其发行时,他作为一名制作人而更为人所知,其“高品质但简约”的风格与日益流行的趋势背道而驰——他使用模拟设备进行录制(他典型地表示,“去他妈的数字”),蔑视日益增加的使用均衡器和压缩,将人声在混音中保持较低的水平——否则,他认为,这就相当于“迎合商业利益”,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吉他的声音和节奏部分的冲击力上——并且非常注重捕捉“声音”通过在房间周围放置老式麦克风来模拟房间的形状。 无论 Albini 对他们的音乐有什么看法,他在《Surfer Rosa》中的作品让 Pixies 听起来非常强大:感觉就像乐队正在现场演奏,离你的脸只有几英寸远。 在 PJ Harvey 的《Rid of Me》中,他的制作与 Harvey 向更黑暗、更发自内心的基调的转变完美匹配:它放大了音乐中怒目而视的紧张感和宣泄释放的时刻。
并不是每个人都对他的做法印象深刻:Nirvana 聘请了 REM 的制作人 Scott Litt 来重新混音 In Utero 中的几首曲目,这让 Albini 非常反感; Fugazi 重新录制了 Albini 制作的整张专辑《In on the Kill Taker》; 埃尔维斯·科斯特洛 (Elvis Costello) 曾认为阿尔比尼让 PJ Harvey 听起来“像狗屎一样”,并补充道“那家伙对制作一无所知”。 另一方面,涅槃后,他成为了大艺术家的首选人物,这些艺术家希望表现出一定的前卫性和对地下酷炫的熟悉,或者想对他们的主要唱片公司的出钱人进行冷嘲热讽:他与吉米·佩奇(Jimmy Page)合作,罗伯特·普兰特(有人怀疑是受后者的授意)在 1998 年的《走进克拉克斯代尔》中与垃圾摇滚乐队 Bush 合作。
如果说他在某些方面被视为一种信誉奖杯,那么他似乎却毫不在意。 他收取固定费用——对于大厂牌艺术家收取更高的费用,对于较小的乐队收取较低的费用——宁愿不被认可,拒绝收取版税积分,显然会与任何联系他的艺术家合作,并拒绝与他们的决定争论:在卢克在海恩斯的自传《Bad Vibes》中,这位前 Auteurs 主唱回忆道,阿尔比尼接受了乐队提出的任何建议,并用了一句“当然——我是你的妓女”。 在此过程中,他与一系列广受赞誉的另类摇滚明星合作——Low、Mogwai、Plush、Will Oldham、Nina Nastasia、Manic Street Preachers、Joanna Newsom——以及一些对他产生影响的人:改革后的 Stooges 和《廉价把戏》,《他是个妓女大黑》已经翻唱过。
与此同时,Shellac 保持着断断续续的专辑流——2000 年的《1000 Hurts》,其中包括臭名昭著的开场曲《Prayer to God》,以及 2007 年的《Excellent Italian Greyhound》,其中收录了《The End of Radio》,这是三人组掌握的令人震惊的八分钟例子这两部作品都受到强烈推荐——而阿尔比尼经常因为他对独立于音乐产业的坚定观点而受到追捧:无论音乐产业发生多大的变化,他似乎从未动摇过,就像他自己的音乐始终不妥协一样。 他唯一改变的似乎是他对《卫报》所说的“他以前的坏自我”的看法,以及他愿意冒犯别人的行为。 “我无法为其中任何一点辩护,”他说。 “这一切都来自于一个享有特权的人,他永远不必遭受那种语言中所体现的任何仇恨。”
但他的道歉甚至有一种毫不畏缩和不妥协的感觉。 他没有为自己找任何借口——“我不想说的一件事是‘文化发生了转变——请原谅我的行为’…… 我当时错了”。 就其本身而言,这是一种非常史蒂夫·阿尔比尼式的否认,尤其是他对自己这样做是为了以任何方式讨好的想法犹豫不决。 “这与被人喜欢无关,”他坚定地说。
1715214136
2024-05-08 20:40:19



:quality(70)/cloudfront-eu-central-1.images.arcpublishing.com/irishtimes/VTISDXW7ZDDC2LX6TRE7PBR5DI.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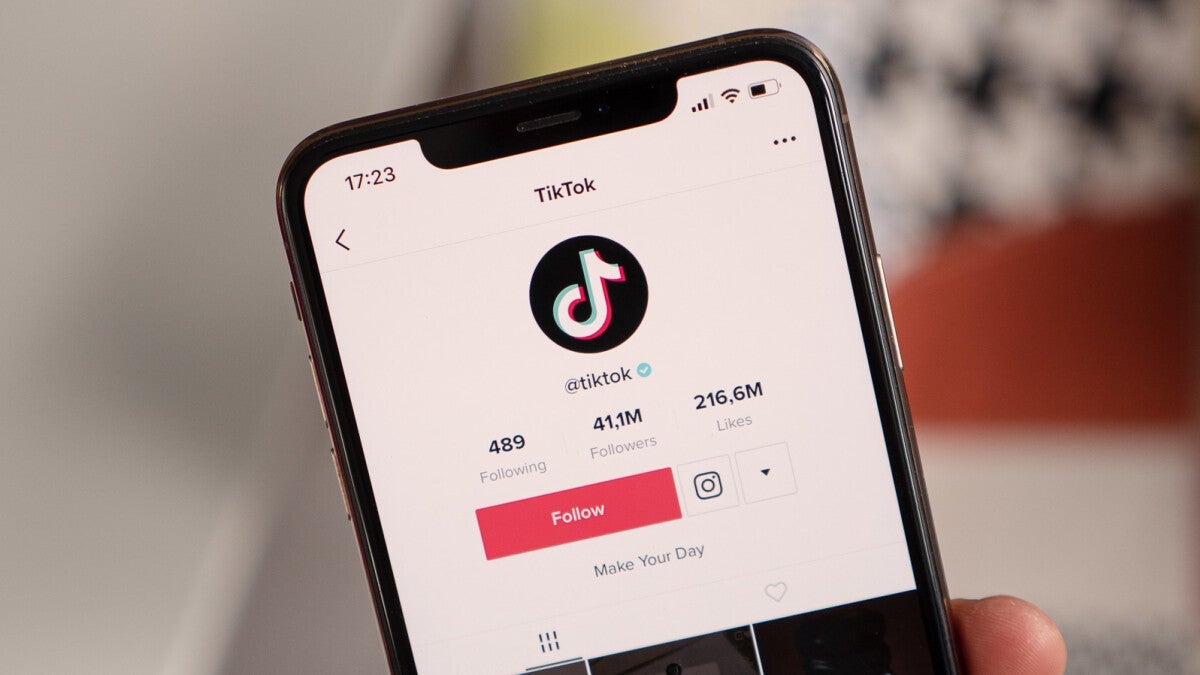

:quality(70)/cloudfront-eu-central-1.images.arcpublishing.com/irishtimes/H6R6WC2L6JC4VICS5HOH4OQ6ZE.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