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案中,最高法院废除了宪法赋予的堕胎权两年后,美国大法官们发布了两项裁决,在美国生育权利前景黯淡的背景下,这些裁决似乎让人稍稍感到安慰。在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诉希波克拉底医学联盟案中, 发布 本月初,法院一致驳回了一群反堕胎医生对 FDA 为简化药物流产所用药物米非司酮的获取而提出的挑战。(近年来,该机构允许在怀孕后期使用米非司酮,并取消了亲自开具该药的要求。)AHM 的投诉主要基于 Brett Kavanaugh 为法院撰写的所谓“复杂因果理论”:该组织在没有实质证据的情况下辩称,FDA 的改变使药物流产变得不那么安全,增加了患者出现并发症的几率,使他们更有可能需要紧急护理,这增加了因道德原因反对堕胎的医生提供这种护理的可能性。法院裁定,这些医生中没有一个人真正面临过这种道德困境,而且在这一系列偶然事件中,没有任何一个事件符合宪法第三条的规定。
法院审理的另一起与堕胎有关的案件是莫伊尔诉美国案,该案围绕着爱达荷州法律与联邦《紧急医疗救治和劳工法》(埃姆塔拉),该法案要求接受医疗补助资金的医院为任何面临“身体机能严重受损”风险的患者提供稳定的紧急护理。埃琳娜·卡根写道:“这两部法律之间的差距在于,继续怀孕不会危及妇女的生命,但仍使她面临严重健康后果的风险,包括失去生育能力。”爱达荷州不同意这一观点,她在一份简报中辩称 埃姆塔拉 将把急诊室变成“不受州法律管辖、而是由医生判断管辖的联邦堕胎区,按照美国政府按需堕胎的规定执行”。
此案体现了在严苛的后多布斯法下工作的医生所面临的困境。自多布斯法以来,限制或禁止堕胎的 22 个州已将保护孕妇生命的例外情况编入法典,但有六个州没有将保护孕妇生命的例外情况编入法典。 健康 患者:阿肯色州、爱达荷州、密西西比州、俄克拉荷马州、南达科他州和德克萨斯州。尤其是在这些州,堕胎法经常造成一种残酷的模糊性,即紧急堕胎何时是允许的——例如早期先兆子痫、胎盘早剥或羊膜囊早破(一种称为 可编程只读存储器)足以危及患者的生命吗?如果死亡似乎并非迫在眉睫,那么感染、子宫切除、大出血或多器官衰竭的风险很高或接近肯定,可能不足以让医生遵守法律。(正如一位母胎医学专家在 2022 年告诉我的那样,“这些法律假定了医学上不存在的确定性。这种情况有多‘危及生命’——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最简单的方法是总结 6–3 结果 在 Moyle 一案中,法院暂时允许爱达荷州的医院提供紧急堕胎服务,但保留对该州是否必须永久允许他们这样做的判断。该裁决的做出过程非常曲折——在正式发布的前一天,该裁决曾在法院的网站上短暂发布。地方法院已对爱达荷州的法律发出初步禁令,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拒绝暂缓执行该禁令。最高法院也可以拒绝,但他却批准了移审令,并在审理此案期间允许该法律生效。然后,在一份只有一行字的全体法官意见中,法院取消了暂缓执行令,而没有对案情作出决定,称该令状“批准不当”。
多数法官对如何定义不顾后果有不同的看法。三位自由派法官认为,该令状是错误的,因为联邦法律明确规定了紧急堕胎护理。但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与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和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共同提出,要求撤销该令状,因为自法院受理此案以来,爱达荷州和联邦政府都澄清了各自的立场;例如,爱达荷州略微软化了原始法规的措辞,而美国则明确规定了医生在符合以下条件的情况下的良心例外情况: 埃姆塔拉巴雷特写道,法官们“不应该抢在下级法院之前,尤其是在如此重要的事情上。”(现在她告诉我们!)凯坦吉·布朗·杰克逊(Ketanji Brown Jackson)在部分同意、部分反对的意见中写道:“实际上,法院的干预意味着爱达荷州的医生被迫退后一步,看着他们的病人受苦,或者安排将他们的病人空运出爱达荷州。”杰克逊补充道,“这场持续数月的灾难完全没有必要。”
塞缪尔·阿利托代表少数派发表意见,认为联邦法律并不要求在任何情况下进行堕胎护理;他的立场主要基于以下事实: 埃姆塔拉的文本中包含了“未出生的孩子”这一短语。阿利托在他的异议中一直强调这个短语,就像他和尼尔·戈萨奇在口头辩论中所做的那样;他认为这是一个陷阱,或者是一个弗洛伊德式的失误,他的坚持强烈暗示了阿利托对胎儿人格的同情。在阿利托看来,因为 埃姆塔拉 为产前护理做好准备,医生必须以某种方式在相互冲突的健康利益之间取得平衡,例如,一名怀孕 20 周的妇女患上先兆子痫——这使她面临中风、肾脏和其他主要器官衰竭以及死亡的风险——和她几乎注定要夭折的胎儿。“毫无疑问,堕胎‘未出生的孩子’并不能保护它免受危险,”阿利托写道。(他保留了引号,好像在说,“这是联邦政府的话,不是我的话。”)
好消息是,只有戈萨奇和克拉伦斯·托马斯与阿利托的意见一致,而其他三位保守派法官则持相反意见。但正如杰克逊指出的那样,莫伊尔案的判决对其他堕胎限制严厉但模糊的州的患者没有任何帮助——例如,德克萨斯州第五巡回法院于 1 月裁定: 埃姆塔拉 并不强迫医院违反州法律提供紧急堕胎服务。杰克逊没有掩饰她的沮丧,因为爱达荷州的案件在法院的审理中被搁置了几个月,并在法庭上进行了详尽的辩论,现在将推迟到以后——也许直到总统竞选结束后,在这场竞选中,堕胎权被证明是另一支队伍的制胜法宝。她写道,“这个法院会不会在一个相对更方便的时间点重新审理和重新讨论我们现在正在考虑的相同论点?”如果杰克逊的假设是正确的,德克萨斯州的 埃姆塔拉 案件与莫伊尔案非常相似,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审的案件。她接着说:“今天的判决对爱达荷州的孕妇来说不是胜利。这是拖延……本法院有机会为这一悲惨情况带来澄清和确定性,但我们却浪费了它。”
在 Moyle 案的口头辩论中,阿利托询问总检察长伊丽莎白·普雷洛加 (Elizabeth Prelogar),她是否会“质疑医院对未出生的孩子负有责任的事实,因为妇女希望怀孕足月”。除了加强阿利托对胎儿人格的亲和力之外,这段文字还因其对堕胎患者可能“想要”什么的假设而引人注目。阿曼达·祖拉夫斯基 (Amanda Zurawski) 是最近一起案件的首席原告 挑战失败 德克萨斯州堕胎法的支持者,以及拜登总统毁灭性竞选广告的核心人物,遭受了 可编程只读存储器 怀孕 17 周时,她被拒绝堕胎,因为胎儿超声检查仍检测到心脏活动。几天后,祖拉夫斯基陷入感染性休克并生下了一个死胎女婴。“感染造成的疤痕非常严重,她需要手术重建子宫,并且失去了一条输卵管的使用能力,”德克萨斯州最高法院的简·布兰德写道,尽管如此,这份意见书还是解除了对该州《人类生命保护法》的禁令。布兰德在判决书中写道,任何在这种极端情况下犹豫提供堕胎护理的医生都是“完全错误的”。看来,那些担心因实施堕胎而被起诉的医生——如果他们对法律允许的内容猜测错误,他们可能会面临六位数的罚款、监禁,甚至失去执照和生计——只需要回去更仔细地阅读德克萨斯州的法规。
可以肯定地说,给孩子取名为 Willow 的 Zurawski 想要“让怀孕顺利进行”。她是否也“想要”堕胎——或者她需要堕胎?对于 Bland 来说,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对于其他人来说,这个问题的前提是错误的。6 月,美国反堕胎妇产科协会首席执行官 Christina Francis 告诉参议院委员会,“堕胎不需要合法化,以确保我们能够为患者提供优质的医疗保健。” Francis 提倡对处于危险中的孕妇进行引产并“简单地生下孩子”,她说,这“比堕胎快得多,可以改善母亲的结果。”(简单而快速——这就是我所说的分娩。)
弗朗西斯的行医行为暗中遵循着天主教的一项教义,即双重效应原则:做坏事(比如在胎儿能够存活或接近胎儿能够存活时引产)在道德上是允许的,只要它是做好事(保护患者的健康)的不良后果。这七位大法官——包括保守派多数派中的所有六位——可能都很熟悉这个原则,因为他们都是在天主教堂长大的。他们可能还听说过意大利儿科医生吉安娜·贝雷塔·莫拉的故事,她是胎儿的守护神。当莫拉怀上第四个孩子时,她被诊断出患有危及生命的子宫肿瘤,并被建议切除子宫——根据双重效应的逻辑,这是一种可以接受的治疗方法。但莫拉选择足月分娩,在生下一个健康女婴一周后死于败血症,留下她的孩子没有母亲。 2004 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莫拉封圣的布道中向她致敬:“通过吉安娜·贝雷塔·莫拉的榜样,愿我们这个时代重新发现夫妻之爱纯洁、贞洁和硕果累累的美丽。”重新发现的时刻可能就在我们身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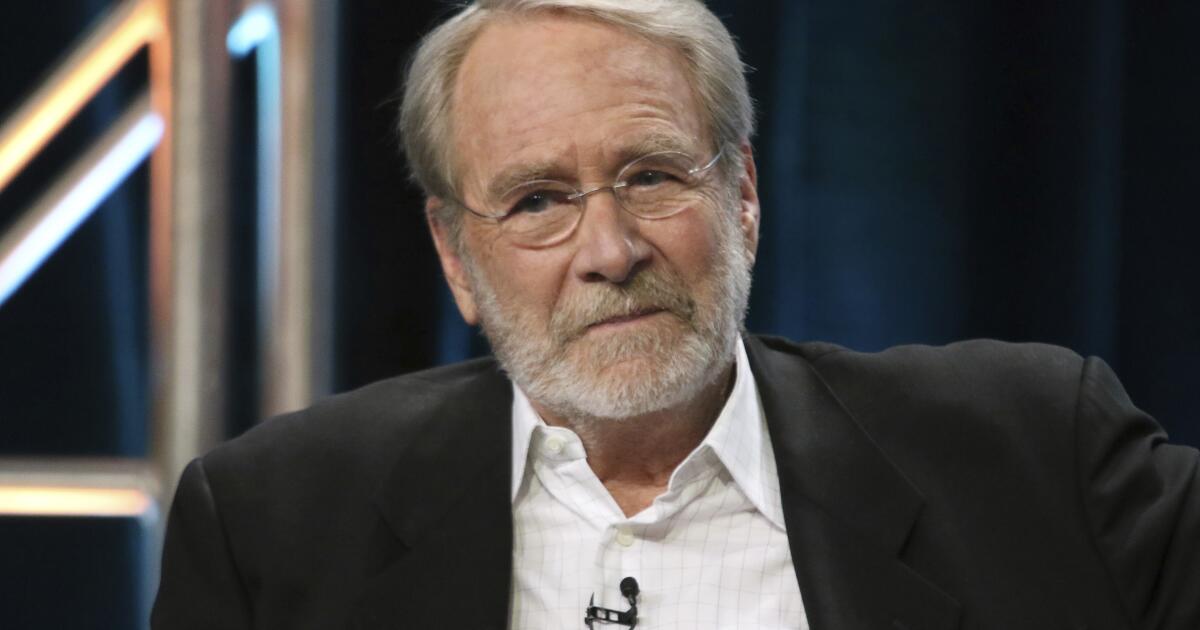


/cloudfront-eu-central-1.images.arcpublishing.com/lexpress/BBYPQZFIVRF6RKZZ6HW5WACTFQ.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