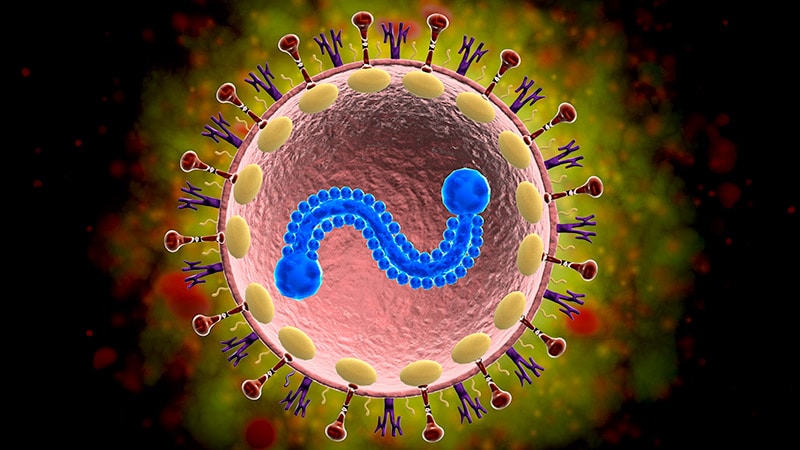那一年的圣诞派对很热闹。在一次派对上,我遇到了几位我一直很钦佩的作家。这可能有点棘手,但他们都很可爱。食物也很美味,不过我把一个迷你烧烤三明治掉在了我穿的新白衬衫上,而且很可能永远也洗不掉油渍。
下一周的另一场聚会上,我被介绍给大都会博物馆的一位馆长。我们谈到了那些把汤和油泼到心爱的画作上的人,他们希望引起人们对气候变化、营养不良或其他原因的关注。然后我得知,他很快就要去非洲旅行了,在非洲旅行时,你带的不是枪,而是相机。
“你计划这件事已经好几个月了?”我问。
“实际上,过去几周一切都已经完成了,”他告诉我。
在回家的地铁上,我用一种假装撅嘴的语气对休说,我用它来挑战极端的不公正——比如,其他夫妻去度假,而本该是我们——“为什么不能 我们 去探险吗?
一个月后,我们坐在一辆敞篷四轮驱动车里,周围围着七头狮子,但似乎没有一头狮子在乎我们。它们全都是雌性,我很好奇,当我事后写到这件事时——我肯定会写——我是否会因为使用“母狮”这个词而受到指责。
“这就像称呼某人为‘女服务员’或‘空姐’吗?”我低声问坐在我旁边画草图的休。“人们会说,‘你为什么一开始要提到他们的性别?为什么你不能只说‘狮子’然后就这样了?’”
在我看来,性别很重要,因为雌性承担了大部分的狩猎任务,因此当它们距离你八英尺远并且能闻到你的气味时,会更加可怕。
回到营地后,我查阅了相关资料,发现关于是否应将母狮称为“母狮”存在一些争议。当然,这些争论并不来自大型猫科动物。这些动物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它们的顽皮,一只会悄悄靠近另一只,轻轻地拍打它,或者翻身仰面,爪子高高举起。我们静止不动了大约十分钟,七只动物中的一只走到我们的四轮驱动车前面,弯腰排便。我以为,就像花坛里的猫一样,它会把粪便掩盖起来,但没有。就在它回到其他动物身边的那一刻,一只豺狼从高高的草丛中冲出来,用嘴叼着粪便,正要逃跑时,一只鬣狗介入了,一场斗争随之而来。
“在…之上 粪“?”休低声问道。
我们可能在那里呆了几个小时,愉快地观察着,但后来又有一辆四轮驱动车停了下来。车上的乘客都疯了:“七只母狮!”休和我看着新来的母狮,脸上的表情好像在说,嗯,它们是我们的。好像是我们亲自把它们聚集在那里的。然后另一辆四轮驱动车停了下来,然后又停了一辆。
我不知道那天下午有多少辆车在马赛马拉漫游。这是一个五百八十三平方英里的自然保护区,所以即使有另外一千辆四轮驱动车,我们可能也看不到其中的几辆。六月到十月是肯尼亚游猎最繁忙的季节,而这是二月初。天气很热但不潮湿,车里有三个人:我、休和我们二十六岁的导游道尔顿,他是马赛部落的成员,穿着一件苔绿色的衬衫,衬衫的右胸口袋上绣着我们住的地方的名字。他的裤子是卡其色的,长及膝盖,搭配及踝高绒面靴。
道尔顿的头发剪得很短。他的头几乎是圆形的,下排牙齿缺失了几颗。“你想看什么?”那天早上,在机场接我们时,他问道。
“一只熊猫,”我告诉他。
在开车回营地的九十分钟里,我们看到了每只“狮子王”然后还有一些。他们只是 那里就像野餐里的蚂蚁,只不过它们是大象和长颈鹿。我们看到了斑马、豹子、角马和疣猪,它们都在这片长满青草、看似无边无际的平原上吃草、休息或逃跑。
“你看到猎杀了吗?”其他四轮驱动车里的人——夫妇俩带着哈勃望远镜大小的相机镜头——会问。很快他们就意识到七只母狮是不够的。他们必须让血从嘴里滴下来。
“第一天,我们看到一只狮子在吃一头角马,”我告诉他们。
这就像说你看到狮子吃三明治一样。奖品是看着狮子扑向猎物,撕开它的喉咙。“就在上个月,午夜刚过不久,两只狮子就在你的帐篷旁边打死了一只斑马,”为我们办理入住手续的女士指着栏杆对面的阴凉峡谷告诉我们。营地建在塔莱克河的河岸上,这条河因为最近的降雨而涨水,但仍然缓缓流淌。营地周围没有围栏。野生动物来来往往,虽然白天我们看到的只有鳄鱼和猫鼬。行动是在天黑后发生的,所以晚上,我们必须由手持长矛的马赛族人护送我们从帐篷到公共区域。最危险的动物——道尔顿称之为“最致命的”——是河马。几年前我从一部自然纪录片中了解到这一点,并感到惊讶,因为在我看来,它们总是看起来很开心,几乎就像在微笑一样。
我们在肯尼亚见过无数的河马。“它们只想进入我们的游泳池,”物业经理史蒂文告诉我们。“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将 绝不 把他们赶出去。”
他带我们参观,领着我们从水培菜园——“农场 善良的,”它被称为——到休闲区。我看着那个负责看守我们经过的池塘的人。“河马闻起来像什么?”我问。
史蒂文想了一会儿。“牛。”
总共有九个帐篷。“现在还有很多其他客人吗?”我问为我们办理入住手续的女士。
“我们这里没有客人,”她笑得我都看见了她的牙龈,对我说,“只有家人。”
哦,不,我想,一个人去狩猎不是为了 逃脱 那种话?同上”农场 善良”。
如果我知道我必须早起,我通常很难入睡。休和我睡觉的地方是帐篷,就像 Shake Shack 是真正的棚屋一样。倾斜的天花板最高处有 12 英尺,除了俯瞰河流的露台外,我们的地板面积足有 900 平方英尺——是真正的地板。有电和 Wi-Fi。有饮用水。有浴缸、淋浴和厕所。免费洗衣服务。食物很棒。我们早上很早和下午很晚才出去,所以我会去睡觉,因为我知道我们需要在 6 点与道尔顿见面 是,我躺在床上,休在我旁边打呼噜。我这次旅行带的书是“安迪·沃霍尔日记”,这完全不符合拍摄地点的定位。而且,看《天桥骄子》前几季也没什么意义。毕竟,我们是在肯尼亚,能听到帆布墙那边各种生物的咆哮、呻吟和叫喊声。
第一天晚上,我拿起 iPad 看了一部关于狒狒的纪录片。这不是那种给动物起名字并低声谈论它们的节目(“……但丹尼斯不会轻易放弃”)。不过,它并没有我想要的那么有趣。最精彩的部分是,这个群落的继承人,一只四个月大的雄性狒狒被入侵者杀死,它的母亲带着它的尸体到处走,直到它只剩下一片毛皮。
第二天下午,我们碰到一群狒狒在河边休息。它们至少有三十只,很多背上还背着小狒狒。“拿出你的相机,”道尔顿一边说,一边关掉了四轮驱动车的引擎。我从一开始就告诉他,摄影不是我的强项。
“我不会拍一张照片,”我保证道。
“即使遇见一头犀牛也不行吗?”他问道。
“即使我们看到一只灰熊和一只母灰熊搏斗,我们也不会这么做,”我告诉他。
道尔顿一直以为我会屈服,但我从来没有屈服,至少在肯尼亚没有。后来,在坦桑尼亚,我会拿出手机,但不是针对动物。而是为了看加油站墙上的标语。标语上写着“禁止吸烟”。
我们营地的一名警卫埃文也注意到我没有拍照。他身材瘦削,相貌英俊,穿着传统的马赛服装,由两块长方形的格子布组成,每块布的颜色都不同。他脚上穿的是旧轮胎制成的凉鞋。他看上去很出色,仿佛穿着 Comme des Garçons 的衣服。当我称赞他的衣着时,他脱下了上面的布料,这块布料几乎像披肩一样披着。“来,试试看,”他说。
我想解释一下,在美国这被称为文化挪用。
我可以想象他会问:“那是什么?”
说实话,我自己也从未理解过。“我认为当你在玉米卷饼上放上蓝纹奶酪时,它就变成了这样”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解释。
“其他人都在不停地拍照,”埃文说着,拿回了那块布料,听起来,即使没有受伤,至少也有点被低估了。“那你为什么不呢?”
“我习惯把事情记下来,”我告诉他,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给他看。“比如,今天早些时候我写了……”我看着一页纸,呻吟了一声。就好像一个只有两根手指的人——一只手一根——写下了这些。在碰碰车里。
我在马赛马拉从未见过铺好的路。有几条路足够宽,可以容纳两辆车,但仍然像我们经常走的几乎看不见、经常被洪水淹没的道路一样崎岖难行。在去野生动物园之前,我最大的担心是我无法锻炼。我们不允许徒步走出营地,所以我担心为了满足我每天的 Apple Watch 最低使用量, 一万步——大约四英里半——我必须连续几个小时在甲板上来回走动。道尔顿在飞机跑道与我们会面的那天早上,我已经走了两英里半,而当我们到达营地时,我奇迹般地走了两倍的路程。似乎我的手表把颠簸的道路和由此引起的颠簸误认为是步行。这对我的步数来说很棒,但对写作来说却很糟糕。
只有当我们停下来时,我才能记录下清晰的东西。话虽如此,我的笔记并不总是像我预期的那样有启发性。“‘Alt’ 是什么意思?”一天晚上,我在晚餐时问休。
他低头看着页面。“不是‘Alt’,”他说。“是‘ALT’。”
然后我想起来了。那天早上我们很早就出门了,观察了一小群鸵鸟。雾蒙蒙的,我指着地平线上模糊的身影。“那是什么?”我问道尔顿。
他顺着我的手指看去,告诉我这很可能是一个 ALT“动物形状的东西”,他解释道。
我的另一条笔记只是简单地写着“哇!”,但我马上就知道它指的是什么——我们旅行的亮点。我们开车经过一群八头大象,其中三头是幼象。它们的体型令人印象深刻,但我已做好准备。令我惊讶的是,它们用鼻子把正在吃的长草从地上拔起的声音是如此美妙。道尔顿关掉了引擎,所以我们只能听到这个声音。“闭上你的眼睛,”我对休说,同时我也闭上了眼睛。如果我要制造一种香水,它的味道会像大象把草从地上拔起的声音一样——既舒缓又令人震惊——每个人都必须拥有它。问题是,它与我多年来想出的任何香水名称都不相配,最好的是 Obsequious。
这八头大象是我们在肯尼亚的最后一天拍的。第二天早上,我们飞往坦桑尼亚,不是为了继续探险,而是为了住在桑给巴尔岛的一个度假村。我们在那里看到的动物只有蜥蜴——有些蜥蜴将近一英尺长——还有休拳头大小的蜗牛。海滩很漂亮——沙子像糖一样白,还有棕榈树。这片土地上站着一些腰带上别着棍棒的人,你一离开,从躺椅走到水边二十英尺,就会有人向你推销东西:一个桶里的煮鸡蛋、一个贝壳、腰果、一次乘船之旅、一幅豹子画、一件印有“没事”上面印着。“我的朋友!”有人会喊道,伸出紧握的拳头,希望你用自己的拳头敲击它,即使你在海里。
这就是为什么我从未去过巴厘岛、毛里求斯或人们冬天去晒太阳的任何其他地方。桑给巴尔的水很温暖,呈现出一种迷人的蓝绿色,仿佛被染色了一样。但住在度假村的人和实际住在岛上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如此之大,以至于你真的看不到其他任何东西。另外,酒店工作人员不停地说着“Hakuna matata”,在斯瓦希里语中意为“不用担心”。
“我可以再喝点咖啡吗?”
“没事。”
“我感觉不太舒服。”
“没事。”
“天哪,好大的蜗牛啊。”
“没事。”
你已经不敢再说任何话了,因为你不想再听到“Hakuna matata”。
任何东西都没有标价。如果你问一袋胡椒多少钱,而对方的回答是“我要给你一个特别优惠”,那你就知道你付的钱太多了。我们遇到的每个人似乎都在赚钱,谁能责怪他们呢?
“往返石头城要多少钱?”一个潮湿的下午,休和我问出租车司机。他给我们报了价,但当我们到达那里时,他声称:“我没说十五万先令”——相当于近六十美元——“我说的是二十万”,这根本不是事实。从大局来看,这不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差额是二十美元,无论如何我都会给他小费——但当你用“哈库纳马塔塔”结尾时,我感觉想哭。
我们本可以在肯尼亚结束我们的假期。是我想加上坦桑尼亚,主要是为了把它列入我去过的国家名单。我到达之前唯一知道的是,在那里当白化病患者并不安全。许多人认为他们是邪恶的,但却非常看重他们的器官和其他身体部位:他们的手和心脏,整条腿。从孩子身上摘取这些器官更容易,所以孩子被绑架和肢解的风险更高。他们的器官被卖给巫医,巫医用它们来制作护身符和药水,比如说,人们可以在寻找贵金属时使用,或者用来改善钓鱼的运气。这听起来太疯狂了。你怎么会这么容易上当?你想知道。 然后你会想到所有的美国人——有些人可能是你的邻居、同事、妻子或叔叔——他们真心相信小肯尼迪没有死于空难,而是活得好好的,并与唐纳德·特朗普合谋阻止克林顿夫妇吸食婴儿的血液。你会想,被屠杀的孩子的腿能帮我找到黄金吗?好吧,我想我听过更疯狂的事情。
这个世界可能是一个野蛮的地方,但这不是你想带回家的教训。是的,我们人类是残忍的,而且常常很危险,但大自然仍然存在,在为时已晚之前,我们需要欣赏它。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和大象一起玩耍,但看看那只栖息在你的喂食器上的鸟,看看那只把鸟从喂食器上赶走的松鼠。看看纽约街头在你面前乱窜的老鼠,看看不知何故被困在你电梯里的蜘蛛。我们都在进行这样或那样的狩猎——只是我们中的一些人没有带着两块鲜艳的马赛格子布长方形布料和细菌感染回来。♦
1718083557
2024-06-10 10:00:00


:quality(70):focal(1211x665:1221x675)/cloudfront-eu-central-1.images.arcpublishing.com/irishtimes/UCAWETCM6RGDRCXDUSG6RENKAI.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