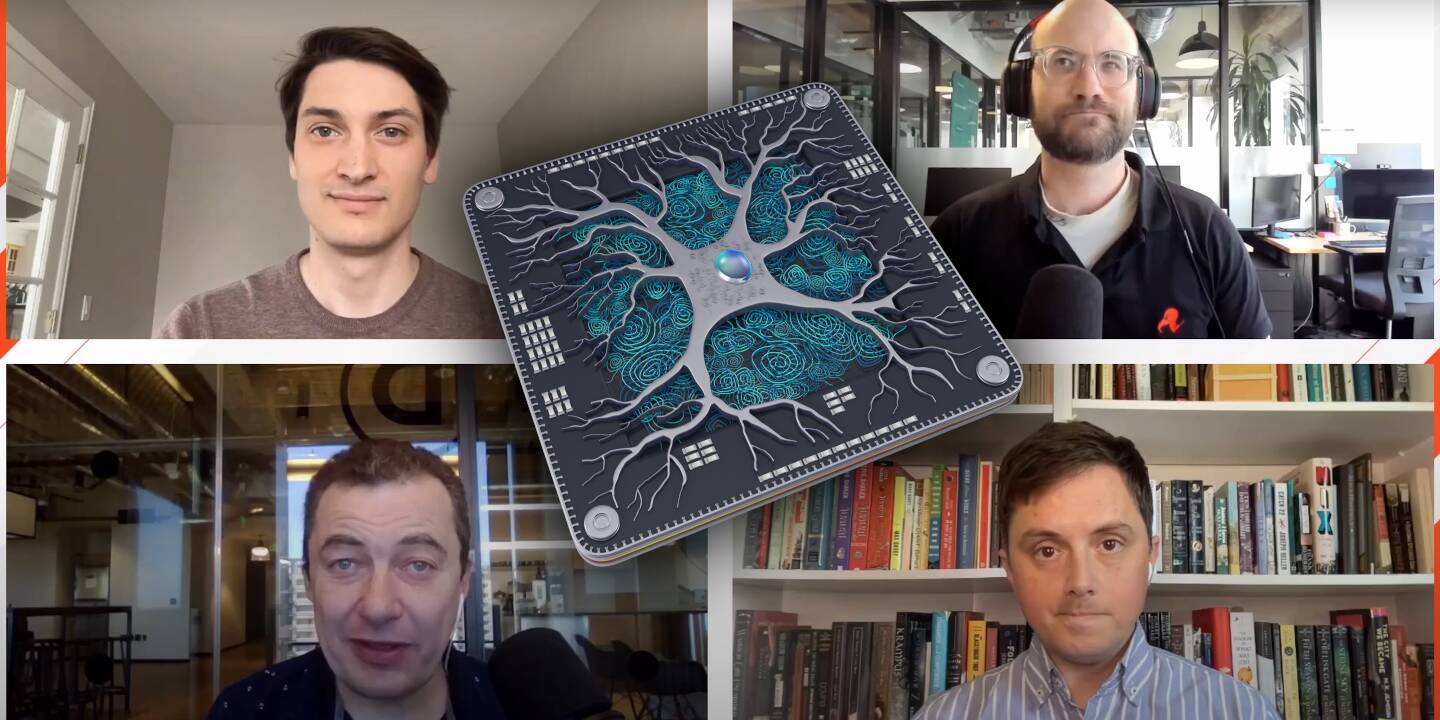加沙战争正在伤害人们的思想和身体。
在这个沿海小飞地,一场日益严重的心理健康危机被大规模的死亡和破坏所掩盖。 三个月以上 以色列的轰炸。 但许多专家认为,心理伤害可能是战争最持久的遗产之一。
多于 25,000 人 据巴勒斯坦卫生官员称,已有人在加沙被杀。 230 万人口中的大多数流离失所, 联合国表示。 根据卫星图像,加沙一半以上的建筑——学校、住宅、大学——都遭到破坏或成为废墟。
1 月 22 日,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发动地面和空中进攻,巴勒斯坦人逃离汗尤尼斯。
(巴沙尔·塔勒布/美联社)
然而,加沙数十年来为建立精神卫生保健系统而奋斗的那些人表示,长期创伤的全部影响,尤其是对非常年轻的人来说,可能要等到战斗停止后才能清楚。
“这场灾难过后,心理创伤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位于约旦河西岸行政首都拉马拉的巴勒斯坦卫生部精神卫生服务负责人萨马赫·贾布尔博士说。 “他们将代代相传。”
加沙有太多儿童的全家都被杀害,医院将他们分类为缩写“WCNSF”——“受伤的儿童,没有幸存的家庭”。
10 岁的达琳·阿纳斯·阿尔·巴亚 (Dareen Anas Al Baya) 在加沙中部代尔巴拉赫住院,周围的人鼓励她使用彩色铅笔表达自己的感受,即使她感觉无法与任何人交谈。
“我每天都画画,”女孩说。她的父母在一次爆炸中丧生,她的腿部受了重伤,但和她的一个兄弟都活着。 一起躲在房子里的女孩的其他数十名直系亲属和大家庭成员也被杀害。
医务人员说,她的一位叔叔幸存下来,正在土耳其接受治疗。
“我希望也许他能把我们带到他身边,”达琳试探性地说。
现场工作人员表示,即使是在这场估计有 12,000 人死亡、两倍以上受伤人数的战争中毫发无伤的儿童,心理影响也无处不在。
“在我们检查的每个帐篷中,我们都发现孩子们强迫性地吮吸手指、尿床、言语困难、食欲不振、做噩梦、无法入睡,”儿童心理健康部门负责人阿拉法特·阿布·马沙伊赫 (Arafat Abu Mashayikh) 博士说。代尔巴拉赫的阿克萨烈士医院。

1 月 17 日,巴勒斯坦人评估以色列袭击加沙地带南部拉法造成的损失。
(法蒂玛·什贝尔/美联社)
青少年是另一个弱势群体,当前的战争——加沙年轻人已经经历过的几场战争之一——发生在他们正在形成信念和社会认同的时候。
“由于这种经历,他们对世界和自身的看法都会被扭曲,”巴勒斯坦心理健康服务主任、临床心理学家贾布尔说。
大人也有苦难。 战前,加沙只有一家精神病院,只有40张床位。 贾布尔说,冲突初期,轰炸导致该设施瘫痪,导致家庭不得不照顾患有严重心理健康问题的亲属,尽管他们疯狂地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以寻求安全。
卫生官员表示,在加沙各地分发精神药物的六个社区精神卫生中心中,有五个在战争的头几周内被迫关门。 远程医疗咨询预约是偏远地区居民的生命线,但很快就因频繁的通讯中断而受到损害。

2024 年 1 月 22 日,在以色列轰炸加沙地带期间受伤的巴勒斯坦人被送往汗尤尼斯的纳赛尔医院。
(穆罕默德·达赫曼/美联社)
战前,巴勒斯坦领土上的精神卫生专业人员和社区外展工作者多年来的努力已经开始消除与精神疾病相关的一些社会耻辱。 医生说,传统上,即使是焦虑和抑郁这样的情况也会让患者和他们最亲近的人感到孤立和羞耻。
一些从业者表示,战争使人们对心理健康的态度变得平等,因为几乎每个人都发现很难应对自己的处境,而且人们更能接受心理斗争。
尽管如此,许多人,尤其是父母,仍然觉得有必要尽可能隐藏自己的痛苦。 一位名叫哈南(Hanan)的七个孩子的丧偶母亲流离失所,住在加沙中部的一个帐篷里,她说她对爆炸感到害怕,但决心不让她的孩子们看到这一点。
48 岁的哈南说:“我总是表现得好像我并不害怕——即使我尖叫,我也会假装在笑。”一家人在一所学校避难后,她试图用学校的承诺来安抚女儿们。一名安全官员表示他们在那里会很安全。 他们很快又不得不再次逃离。
哈南说,有时候,压力太大,她无法承受,她会假装需要去一下营地肮脏的厕所,只是为了休息一会儿。
“我想跑——离开帐篷就跑,”她说。 “我假装想去洗手间,这样晚上就可以出去走走。”

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聚集在加沙地带南部穆瓦西的临时营地。
(哈特姆·阿里/美联社)
健康专家表示,生活在持续的恐惧中也会带来危险,因为极端压力通常会损害决策能力。 在加沙,度过一天需要聪明才智和计划——寻找住所、获取食物、寻找干净的水。
“在战区,一个人的心理健康状况会极大地影响生存能力,”美国陆军预备役上校、犹他大学副教授、精神病学家史蒂夫·萨格登博士说。 “对于处于这种心态的人来说,决策更加保守,他们会立即对事件做出反应,而不是彻底思考问题。”
在加沙,能够为精神痛苦的人提供护理和安慰的人数正在减少——因为他们也受到了创伤。 在医疗系统全面崩溃的背景下,这种损失可能会被忽视,但随着战争的拖延,人们越来越能感受到这种损失。
“加沙的许多人都接受过提供心理‘急救’的培训——护士、全科医生、教师,”贾布尔说。 “但现在,实际上没有人能幸免于失去亲人、家园或财产,因此帮助能力正在减弱。”
卫生专业人士表示,对于加沙的许多人来说,坚忍是渡过难关的唯一途径。 人们在不得不将亲人送葬在废墟下后,可能会怀有终生的负罪感——但在那一刻,人们会觉得无话可说。

逃离汗尤尼斯的巴勒斯坦人于 2024 年 1 月 22 日抵达加沙南部的拉法。
(法蒂玛·什贝尔/美联社)
在拉马拉,贾布尔尽其所能与心理健康领域的同事保持联系。 有时她可以提供一些实用的建议,但有一种情况她觉得特别难以应对。
“就在那时,我认识的一个人失去了很多——他们的孩子被杀了,他们的家被毁了——坚持问我怎么样,我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她说。 “这才是最让人难以忍受的。”
出于安全原因,《泰晤士报》驻加沙特约记者的姓名不能透露。 金是一名特约撰稿人,他在耶路撒冷为这份报告做出了贡献。


:quality(70)/cloudfront-eu-central-1.images.arcpublishing.com/irishtimes/4NB5XJVR5P2U6YTLCETWUV55RI.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