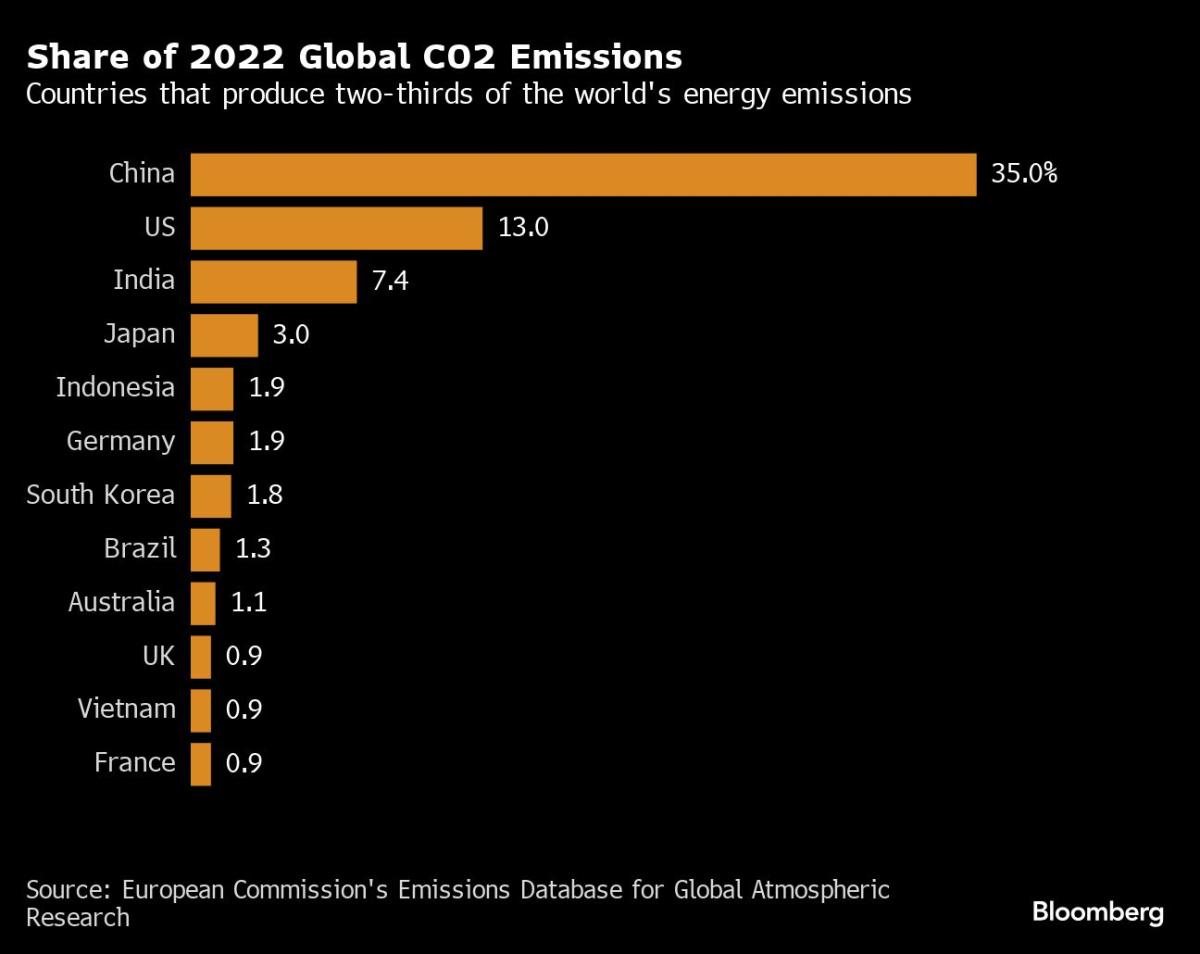几年前的一个压力特别大的一天,当我开车去参加一个重要的工作活动时,我突然出现了严重的抽搐。 这对我来说并不罕见。 我几乎一生都在打嗝,压力很大 总是 加剧了我的抽搐。
这一天,我的鼻息和抽搐完全失控,以至于追尾了一辆汽车。 就在那时我终于去看了神经科医生。 我需要确切地知道是什么让我抽搐。 他告诉我的话——“你患有图雷特综合症”——让我感到震惊。
这也是一种解脱。 从我记事起,我就一直患有与这种情况相关的特有的声音和运动抽搐。 我处理它们的方式就是把它们藏在我的精神密码箱里,埋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 诊断带来了清晰的结果,这意味着我可以以更健康的方式处理我的抽动症——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在 20 世纪 80 年代纽约西部的一个小镇长大,那些令人陶醉的日子充满了消耗臭氧层的发胶、傻乎乎的鲻鱼和糖浆般的合成流行乐。 在我的农村社区,很少有人知道什么是抽动秽语。 我当然没有。
当我十几岁的时候,一个电视节目,可能是“60 分钟”,播放了我和妈妈一起观看的主题的一集。 故事讲述了一名年轻男子在美国某大城市大声喊出脏话的故事。 到那时我已经打勾多年了——事实上,我已经 隐藏 我多年来的抽动症。 但我在这个节目中没有认出自己,因为我从来没有、一次也没有在公共场合说过脏话或大喊大叫。
当我上小学时,一位老师曾经停课告诉我不要发出声音,不要“用头脑做你正在做的事情”。 她实际上在我的同学面前展示了“那件事”,因为我显然惹恼了她并扰乱了她的课程。 每个人的头都转向我,而我则放下了自己的头,感到羞辱。 我不能告诉她我无法控制自己。
在观鸟中,有一种叫做“火花鸟”的鸟,当你第一次在野外看到它时,就会真正让你迷上观鸟。 但这是我的火花时刻, 当我意识到我的抽动并不“正常”并且如果我想的话我需要隐藏它们 是 普通的。
如果我妈妈把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孩子和我联系起来,她也没有提到,我的父母也没有带我去看神经科医生检查。 因为那个电视节目,我错误地认为患有妥瑞氏症就意味着在公共场合大喊脏话。 我了解到这个版本的抽动秽语症被称为粪尿症, 根据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它“只影响大约十分之一的妥瑞氏症患者。” 它并不像流行媒体喜欢描述的那样常见。
对我来说,抽搐一直意味着一种近乎持续的冲动,想要用我的身体做一些事情。 “催促”可能不太适合形容这些头抽动、眨眼、打喷嚏、咕噜声、清喉咙、打舌头等,但这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词了。 从我醒来的那一刻到我入睡的那一刻,我的身体似乎有自己的意志。 在任何特定的时间里,我可能会抽搐 至少 100次。 在压力很大的时候,比如当我追尾那辆车时,我的抽动就像一种寄生真菌,完全控制了我的身体。
没有人愿意在公共场合抽搐或发出奇怪的声音——成为人们伸长脖子看的人。 这家伙怎么了? 你想象他们在思考。 被老师叫出来后,我只想融入其中——变得隐形——因为当你上小学时,你不想被视为一个怪胎。 你想和其他人一样。
我无法停止滴答声,但我发现我可以让它不那么明显。 为了保护自己免受羞耻和尴尬,我开发了一系列隐藏抽动的策略。 我不会猛地摇头,而是把手放在桌子下面,反复摆动手指或握拳。 我不会发出鼻息或喘气声——明显而奇怪的声音——而是轻轻地发出舌头声,就像一个不规则的节拍器。
这些技巧满足了我近乎持续不断的抽动冲动,让我几乎不被人看见。 我在学校里没有像患有抽动症的孩子和成人那样被欺负或嘲笑,但如果我没有学会如何控制抽动症,我可能会受到欺负或嘲笑。
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使用这些技巧。
当我今天出现在公共场合时,我敏锐地意识到我内心的抽动压力,但我已经变得善于压制它,将它封存起来并紧紧地盖住。 在家里,我可以自由地做自己,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故事。 我的抽动来来去去。
六个月前,我开始从嘴里喷出空气,就像有人吹掉脸上的头发一样; 几周后,我开始打嗝,好像要吐痰一样。 就像不速之客不受欢迎一样,当我写下这些话时,这两种抽动仍然伴随着我。 有时,某种特定的抽动会消失,但一年后又会出现,就像一个令人恼火的哥哥,他去上大学了,带着狡猾的笑容和蓬乱的胡子回家。

抽动秽语症无法治愈——您所能做的就是尝试控制抽动。 有多种治疗方法可供选择,包括胍法辛和可乐定等抗高血压药物,以及抗精神病药物利培酮和阿立哌啶等替代药物。 但老实说,我宁愿抽动也不愿这些药物可能引起的潜在副作用。
当我第一次被诊断出来时,我尝试了胍法辛,但我会在半夜醒来,口干舌燥,就像吞下了沙子一样; 我的失眠感觉更像是一种惩罚,特别是因为药物甚至无法控制我的抽动,所以我停止服用药物。 从那时起,我没有选择其他治疗方法,尽管我最近了解到一个有希望的选择,我将尝试称为“抽动症综合行为干预”或 CBIT。 这不涉及任何药物。 相反,它会训练您改变行为并减少抽动。
研究人员 估计 35 万至 45 万美国人患有抽动秽语综合症,而大约 100 万人患有其他持续性抽动障碍。 据说没有足够的证据来确定患有抽动秽语症的成年人数量,因为许多人在青春期后期就不再抽动了。 根据美国妥瑞氏症协会的说法,这种情况“发生在 160 名学龄儿童中就有 1 名 (0.6%), 尽管据估计 50% 的人未被诊断出来”(斜体是我的)。
A 2022 年调查 该组织表示,十分之一患有抽动障碍的儿童“在过去 12 个月内至少尝试过自杀一次”。 这是一个可怕的数字,它说明了许多患有抽动症的人很难对自己的身体感到舒服。 我很高兴今天被诊断出患有抽动秽语症的孩子(及其父母)现在拥有可用的资源(包括支持性社区),可以减少因生活中这种尴尬的事情而受到的耻辱或排斥。
我做到了 不是 我的抽动症会消失。 因为很难公开承认我一直内化并与羞耻相关的东西,所以很少有人了解我的这一部分。 即使您没有受到欺凌或骚扰,伤害和羞辱也会根深蒂固; 它们会形成很容易刮掉的疤痕。
有多少成年人像我一样在雷达之下飞行? 谁像我一样,从来没有摆脱过抽动,却制定了隐藏抽动的策略? 谁没有从美国图雷特协会提供的服务或当今正在进行的丰富研究中受益? 谁因为害怕被揭露为抽动症患者而努力建立真正持久的友谊?

除了抽动症带来的麻烦之外,我过着社会可能认为“美好”和“正常”的生活。 我有妻子、孩子、一份好工作、一栋房子,以及作为一名作家和翻译的创造性生活。 我患有图雷特症,但图雷特症却没有我——尽管我的妻子肯定不同意这一点。 25 年前我们在一起时,我在她面前压抑了自己的抽搐,但你无法向与你同住的人隐瞒这样的事情。 我不再尝试了。 即使在那些夜晚,当我的身体让她难以入睡时,她也会支持我。
由于我一生都在隐藏自己的抽动症,所以我已经成功地融入其中,即使是在工作中与人会面或在舞台上在观众面前朗读或采访作家时也是如此。 但我也经历过深深孤独的时刻。 退缩到自己身边是避免在公开场合尴尬的好方法,但你要付出代价。 最终,你会感觉自己就像是自己生活中的一个幽灵——除了你自己和一些你信任的精心策划的人之外,没有人认识你。 我不容易交朋友。
今年晚些时候,我将出版我的处女作《洛斯曼之书》,在过去的 30 年里,我翻译了十几本丹麦小说,写了无数未售出的手稿。 这是关于一位文学翻译家的故事,就像我一样,患有抽动秽语症,但相似之处仅此而已。 这是一部推理小说,讲述了居住在丹麦哥本哈根的洛斯曼的故事,他参与了一项实验药物研究,以重温童年记忆,希望找到治疗抽动秽语症的方法。 为什么不? 小说的美妙之处在于,你可以想象任何你想要的东西,只要你创造的世界是可信的。
在现实生活中,我无法及时回到过去去安抚那个在小学被点名的小孩,但我已经足够大了,能够理解一些他无法理解的事情:“正常”是一个非常主观的词,一个带有花边的词。有很多假设。 快 50 岁了,我的抽动症(以及控制它们的需要)已经根深蒂固地融入了我的生命结构中。 即使在发表这篇文章之后,我仍将继续在公共场合隐藏我的抽搐。 为什么? 耻辱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尊严与羞辱之间的界限最终是一线之隔——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 我真的很钦佩那些年轻一代,他们可以在 TikTok 或 YouTube 上展示自己,让世界看到。 那不适合我。 但通过在这里分享我的故事,我 能 所做的就是帮助抽动秽语症和其他抽动障碍恢复正常。 像我这样的人,我们就在你身边。 我们所要求的只是 每一个 人类应该:过一种没有评判的生活。
KE Semmel 是十几本丹麦和挪威小说的作家和翻译家。 他的小说和非小说作品出现在 安大略评论文学中心, 作家的编年史, 南方评论, 这 华盛顿邮报 和埃尔斯任何地方。 “钍e 世界和瓦尔瓦拉” 西蒙·弗鲁伦德 (Simon Fruelund) 的著作是他的最新译本。 他的处女作《洛斯曼之书,”将于 2024 年 10 月出版(圣达菲作家项目)。 在线找到他: KESemmel.com 在他的 Twitter/X 页面上, @KESemmel。
您有令人信服的个人故事希望在《赫芬顿邮报》上发表吗? 了解我们在这里寻找什么,并通过itch@>.com向我们发送推介。
支持赫芬顿邮报
我们的 2024 年承保范围需要您
您的忠诚对我们来说意味着整个世界
在《赫芬顿邮报》,我们相信每个人都需要高质量的新闻,但我们知道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负担得起昂贵的新闻订阅费用。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致力于提供深入报道、经过仔细事实核查的新闻,供所有人免费获取。
无论您来到《赫芬顿邮报》是为了了解 2024 年总统竞选的最新动态、对我们国家当今面临的关键问题进行的严厉调查,还是让您开怀大笑的热门故事,我们都感谢您。 事实是,新闻的制作需要花钱,我们感到自豪的是,我们从未将我们的故事置于昂贵的付费墙后面。
您愿意加入我们,帮助所有人免费分享我们的故事吗? 您只需贡献 2 美元,就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无力捐款? 通过创建免费帐户并在阅读时登录来支持《赫芬顿邮报》。
当美国人将于 2024 年参加投票时,我们国家的未来正受到威胁。 在《赫芬顿邮报》,我们相信新闻自由对于培养消息灵通的选民至关重要。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新闻业对每个人都是免费的,尽管其他新闻编辑室却躲在昂贵的付费墙后面。
我们的记者将继续报道这次历史性总统选举期间的曲折。 在您的帮助下,我们将为您带来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强有力的调查、深入研究的分析和及时的见解。 在当前的政治气候下进行报道是我们不会掉以轻心的责任,我们感谢您的支持。
只需捐款 2 美元,即可让所有人免费获得我们的新闻。
无力捐款? 通过创建免费帐户并在阅读时登录来支持《赫芬顿邮报》。
亲爱的《赫芬顿邮报》读者
感谢您过去对《赫芬顿邮报》的贡献。 我们衷心感谢像您这样的读者,他们帮助我们确保我们能够为所有人免费提供新闻报道。
今年的风险很高,我们的 2024 年报道可能需要持续的支持。 您会考虑成为《赫芬顿邮报》的定期撰稿人吗?
亲爱的《赫芬顿邮报》读者
感谢您过去对《赫芬顿邮报》的贡献。 我们衷心感谢像您这样的读者,他们帮助我们确保我们能够为所有人免费提供新闻报道。
今年的风险很高,我们的 2024 年报道可能需要持续的支持。 如果自您上次投稿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希望您考虑再次为《赫芬顿邮报》投稿。
支持赫芬顿邮报
已经贡献了? 登录以隐藏这些消息。
1714492794
#这就是抽动秽语综合症的感觉
2024-04-29 11:48:46



:quality(70):focal(2679x2072:2689x2082)/cloudfront-eu-central-1.images.arcpublishing.com/irishtimes/VTLL6UKL65EOFLVDFUHTKPVP6M.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