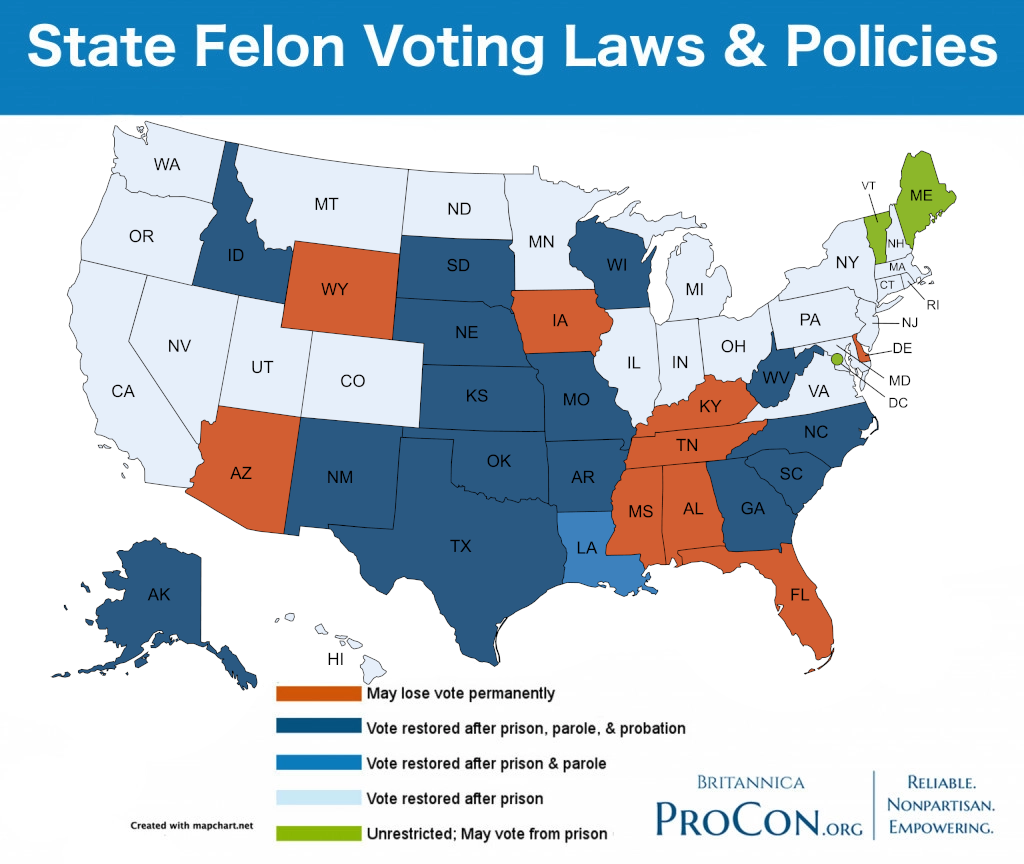H愧疚感必须持续多久? 当我还是个大约 10 岁的男孩时,我有一个足球,我和我的朋友们、我的兄弟们或者我一个人踢了很多年,漫无目的地运球或把它踢到墙上。 这个球赋予了我某种地位,因为我们过去称之为“caser”,但我已经有 40 年没有使用过这个词了。 外壳意味着这是一个真正的足球,里面有橡胶气囊,外面有皮革。 这与随风飘扬的非常便宜的塑料球或由较厚的塑料制成且看起来像盒子的塑料球不同。 后者比前者更受人尊敬,但你知道,它并不是一个案例。
我拥有这个球很长一段时间,从只能进行 5 次保球,发展到可能可以进行 10 次保球。是的,我就是那么有天赋。 那是 70 年代,在这个十年的初期,阿迪达斯为 1970 年世界杯推出了 Telstar 球。 它由 32 块皮革面板制成,由 12 个黑色五边形和 20 个白色六边形组成。 我的 caser 就是以那个 caser 为蓝本的。 这可能是我祖父的礼物,但我不记得它新时的样子,只记得它旧时的样子,当时面板既不是黑色也不是白色,只是棕色,拥有所有颜色被他们赶了出去。
那时,我想要一个新的,一个闪亮的新球,可能是阿迪达斯为 1978 年世界杯制作的 Tango,令人陶醉的是,它的面板少了 12 个。 但我妈妈说不。 她说我的球完全没问题,当它无法使用时我只能希望换一个新的。 她说得有道理。 我的外壳虽然是一种非常无趣的棕色制服,但对于足球用途来说仍然足够圆且足够硬。 在可能是几个小时、几天、几周或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不记得了——我用更大的力气踢这个可怜的东西,希望能加速它的使用寿命。 最终,我发现一些缝线松动了,透过缝线可以看到一点亮橙色的膀胱。
不,我妈说:还好。 随之而来的是进一步的猛烈踢打,但没有产生通货紧缩的黑暗喜悦。 所以我很抱歉地说我做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我把我忠诚的、被爱的、后来不被爱的凯瑟带到一个安静的地方,然后把小刀插入暴露的膀胱。 直到今天,我还能听到我可怜的老球最后喘息时发出的声音——实际上,与其说是喘息,不如说是纯粹的悲伤和失望的叹息。 我让我的妈妈失望了,让我自己失望了,我让我的箱子失望了,在很多方面。 我对那个闪亮的新球失去了所有的想法。 我泪流满面,跑向妈妈。
可怕的讽刺是,正是我羞愧的泪水使我逃脱了对我可怕罪行的惩罚。 妈妈以为我在为球爆裂而哭泣,事实确实如此,但不是她想象的那样。 老实说,我付出的代价是一生的愧疚。 我想那是因为我逃脱了惩罚。 如果我不这样做,我就会受到惩罚,我的罪孽就会以某种方式得到弥补。 如果她看到了我所做的事情,毫无疑问,我会受到一顿猛烈的殴打——实际上,当她读到这篇文章时,一场猛烈的殴打可能会随之而来——而这件事就会得到处理。
事实上,我得到了一个新球,但我永远无法像旧球一样爱它,而且我的灵魂上还有一点橙色的羞耻污点,我永远无法改变。 这对我来说是对的,我妈妈随时都会告诉我。
1713403612
2024-04-17 15:33:05